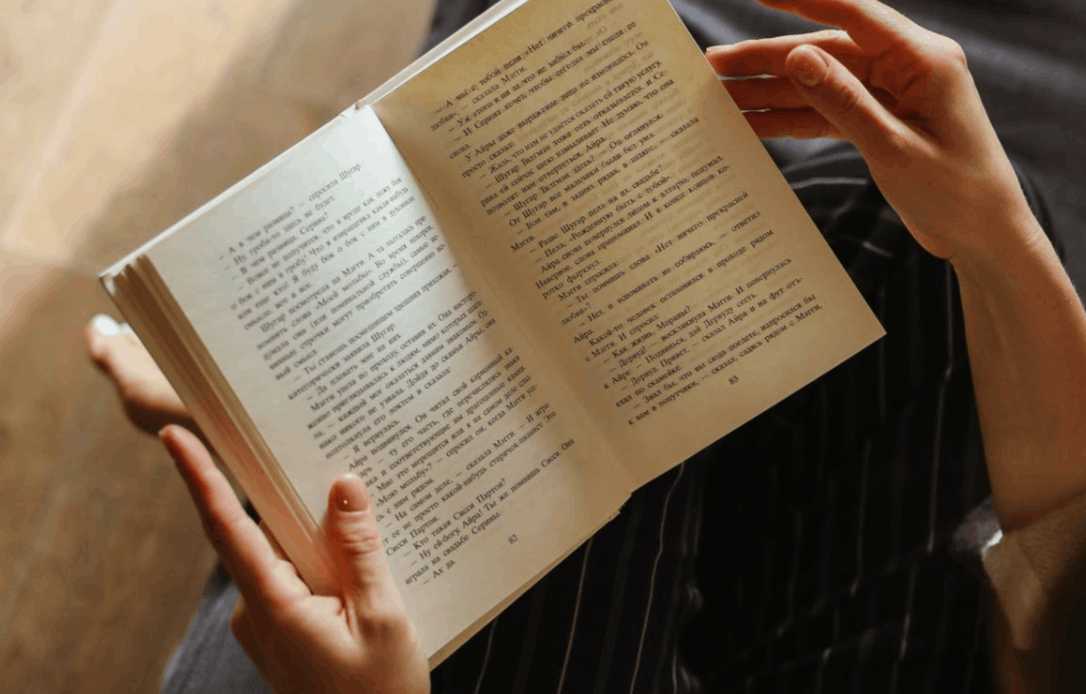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知识金字塔
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知识金字塔模型
1 知识金字塔
正确地理解知识,需要从知识金字塔开始说起,通过多层次的概念梳理,有助于理解知识的内涵。知识金字塔是指“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层次结构(DIKW)模型,也被称为“知识层次结构”、“信息层次结构”等,是被广泛认可的信息和知识模型。
DIKW层次结构用于关联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上下文关系,并标识和描述层次结构中较低级别的实体(如数据)向高级别实体(如信息)转换所涉及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知识金字塔模型中通常隐含着如下假设:数据可用于创建信息,信息可以用于创造知识,知识可用于创造智慧。 而Ackoff [1]认为:该层次结构模型中,每个较高类型“都包括低于它的类型”。

2 相关概念的讨论
多年来,相当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信息和知识的定义和区别上。
(1)信息的本质
因为信息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因此已被许多学科所考虑,包括传播理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信息系统、认知科学和组织科学等。这对信息的性质产生了多种观点。
弗洛里迪(Floridi)建议,“在我们一般的技术概念中,信息是目前最重要、应用最广泛、但了解最少的信息之一”。他确定了六种信息定义方法:沟通理论方法、概率方法、模态方法、系统方法、推论方法和语义方法。
信息哲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其重点是“对信息的概念、性质和基本原理进行批判性研究,包括其动态(特别是计算和信息流)” 。不同的作者给**“信息”一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并且尚未就“信息”**一词达成共识。
(2)知识的本质
关于知识本质的争论同样长期存在,随着知识管理学科的兴起,近年来也聚集了许多势头。
柏拉图首先将知识定义为**“合理的真实信念”,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波兰尼等人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数个世纪的争论。卡卡巴德斯等人利用这些辩论,提出了知识“可以被认为是用于生产性使用的信息”**。知识管理学科与信息哲学学科一样,受到多学科影响,包括:哲学、认知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知识工程、人工智能和经济学。
卡卡巴德斯等人提出了五种不同的知识管理观点,每种观点对知识和知识过程的性质都有不同的立场:基于哲学的、基于认知的、基于网络的、基于社区的、基于量子的。
(3)其他讨论
一些研究还探讨了数据和智慧的本质,但是讨论大多集中在DIKW层次结构中的一个元素上,而不是所有元素以其间的关系。
3 知识金字塔的起源
知识金字塔层次结构模型的首次出现是在艾略特(Eliot)1934年的诗《摇滚(The Rock)》中。该诗中包含两行:
“Where is the wisdom that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Where is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
最近的文献多引用阿科夫(Ackoff)1989年的论文作为层次结构模型来源。阿科夫在题为《From data to wisdom》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数据、信息、知识、理解和智慧的五层次结构,但最近评论家对将“理解”作为一个单独层次提出了质疑。 在文章中,阿科夫定义了数据、信息、知识、理解、智能和智慧等概念,并讨论这些元素之间的相关转换过程。
尽管阿科夫最初是将层次结构作为人类思维的内容提出的,但是大多数这些定义和过程都是从信息系统视角来描述的。 阿科夫提供了如下概念及其相关转换过程的定义:
【数据】
- 数据被定义为表示对象、事件及其环境属性的符号,是观察的产物。
- 在赋予数据一种可用(相关)的形式之前,它是无用的。
- 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差异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
【信息】
- 信息包含在解释(描述)中,可以回答诸如:谁、什么、何时以及多少等词开头的问题。
- 信息系统生成、存储、检索和处理数据,信息是根据数据解释或推断出来的。
【知识】
- 知识就是know-how
- 知识使信息转变为指令(instruction)或操作成为可能。
- 知识可以从其他拥有知识的人那儿传播过来,也可通过指令(instruction),或从经验中提取而获得。
【智能】
- 智能是提高效率的能力。
【智慧】
- 智慧是增加效力(效果)的能力,这与智能有着一定区别。可以说机器具备了一定智能,但不能说它具备了智慧。
- 智慧通过“判断”这一心理功能过程增加价值
- 这表明:道德和审美价值是人固有的,而且具有独特性和个性化特征。
阿科夫的文章并不是唯一有关层次结构的早期文章。
-
克利夫兰[3]较早地提到了在信息科学文献中可以找到的层次结构。
-
与阿科夫几乎同时,Zeleny [4]还讨论了DIKW层次结构,并在层次结构的顶部提出了一个附加的层次,即启示(Zeleny将其定义为智慧)。启示不仅是回答或理解为什么,而且可以进一步实现真理感、对错感,并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接受、尊重并受到制裁。
-
Cooley [5]在讨论隐性知识和常识时也建立了DIKW层次结构。
-
贝林格等人进一步阐述了阿科夫的论述[6],认为理解不是一个单独层次,理解支持从每个阶段到下一阶段的过渡。他们建议,从数据到信息的转移涉及“理解关系”,从信息到知识的转移涉及“理解模式”,从知识到智慧的转移涉及“理解原理”。
-
在信息系统和知识管理教科书中, Chaffey和Wood [7]显示了图2中的层次结构,以及附加的意义和价值轴。
-
Pearlson和Saunders [8]提出,在层次结构的较高级别中,人类输入增加,而计算机输入减少(图3)。
-
Jashapara [9]显示了具有层次的层次结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和真理。 Choo [10]绘制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图,侧重于信号、数据、信息和知识之间的转换过程(图4)。



上述文献资料在层次结构表述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1)关键要素是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
(2)这些关键要素实际上总是按相同的顺序排列,尽管某些模型提供了附加的阶段,例如理解或启发
(3)通过确定适当的转换过程,可以用较低的元素来解释层次结构中较高的元素
(4)隐含的挑战是:理解和解释如何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如何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智慧。
4 归纳和总结
(1)数据的定义
在已查提供数据定义的文献中,总体有如下的建议: Choo [10]建议,数据通常是较大的物理系统(例如书籍或仪表板)的元素,这些物理系统提供有关注意哪些数据以及应如何读取这些数据的线索。Jashapara [9]和Choo [10]也介绍了信号的概念。 Jashapara [9]建议通过感官从外部世界获取数据,并尝试通过我们的经验来理解这些信号。 Choo [10]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专门将信号识别为数据的来源,并提出了将信号转换为数据的感知和选择过程,一起称为物理结构。有趣的是,这些定义主要是根据缺乏数据的情况来进行的。 总体来说,数据缺乏意义或价值,是未经组织和未经处理的。它们为根据数据定义信息奠定了基础。
(2)信息的定义
信息系统书籍倾向于关注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关系,经常根据数据来定义信息。各种定义中的格式、结构、组织、含义和价值的概念具有以下特征: Bocij等[11]同意以下发现: Pearlson和Saunders [8]提出,对数据的这种处理需要对分析类型做出决定,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具有相关性和目的,必须在接收和使用信息的范围内考虑信息。 Boddy等指出意义的概念是主观的,一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而另一个人可能将其视为没有特殊意义的数据。 Beynon-Davies认识到信息的含义既重要又对许多解释开放,因此着手进行基于符号学或符号学的解释。他认为信息可以看成是符号的体现,并讨论了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和实证学的要素如何指导人们对交流和信息的思考。 五本知识管理教科书也定义了信息,这些定义也定义了与数据有关的信息。例如: Jashapara也同意Boddy等人的观点,即由人类接收者确定收到的消息是数据还是信息。Choo [10]称此过程为“认知结构”,该过程将所感知的事实和消息赋予意义。 总而言之,在信息系统教科书和知识管理文献中,信息都是根据数据进行定义的,并且被视为组织或结构化的数据。处理为特定目的或上下文提供了数据相关性,从而使其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有用和相关。
(3)知识的定义
关于知识的定义性陈述通常要比对数据或信息的定义性陈述复杂得多。实际上,许多知识管理文本对知识的本质、知识的各种表示形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扩展的定义性讨论,并对知识的本质进行了哲学辩论。这些辩论使关于知识本质的定义性陈述更加困难。确实,正如某些文本所认为的那样: 六本信息系统书籍提供了有关知识的定义性陈述,经常根据数据和信息来定义知识。例如:
珀尔森和桑德斯都认为知识是人类思想中的信息,包括反思、综合和背景:
“ Knowledge consists of that mix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values, experience, and rules […] Knowledge involves the synthesis of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ver time. The amount of human contribution increases along the continuum from data to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 其他作者还通过“添加的成分”来讨论知识和信息之间的关系: Jashapara和Newell等提到了信息的语义方面在知识创造中的重要性。这些语义方面是建立在我们对现实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之上的。一些知识管理课本讨论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区别: 通常,他们同意隐性知识被嵌入个人中,而显性知识则被编码和记录,并因此被设计用于共享。总而言之,人们一致认为知识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然而,这些作者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观点。知识通常是根据信息来定义的,但是有些讨论了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而另一些则确定了“添加的成分”。将信息转换为知识的过程被不同地描述为: “添加成分”的定义不同地表明知识是: 总结这些定义,知识可能会被视为信息、理解、能力、经验、技能和价值观的结合,但是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作者都提到了所有这些要素。知识管理资料比信息系统资料更有可能讨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差异。通常,它们区分嵌入在个人中的隐性知识和驻留在文档、数据库和其他记录格式中的显性知识。
(4)智慧的定义
Jashapara提出智慧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时,大部分人可能会同意。它可能与人类的直觉、理解、解释和行动有关,而不是与系统有关。提到智慧的作者都认识到智慧的重要性,以及参考智慧将信息和知识管理进行情境化的重要性。 Jessup和Valacich将智慧视为积累的知识,它使您能够了解如何将概念从一个领域应用于新情况或新问题。在知识管理文献中,阿瓦德(Awad)和加兹里(Ghaziri)提出“智慧是最高的抽象水平,具有远见卓识和超越视野的能力”。贾沙帕拉(Jashapara)提出了道德问题:‘智慧是在任何给定情况下都可以采取批判性或实际行动的能力。它基于与个人信仰体系有关的道德判断。这些文本中关于智慧概念的相对有限的讨论表明,对关于智慧本质的讨论还比较有限。
5 讨论
(1)各层次定义之间的关系尽管数据和信息都可以充当知识的输入,但人们一致认为数据、信息和知识应相互定义。这种共识重申了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层次结构的概念。
(2)转换过程关于将数据转换为信息以及将信息转换为知识的过程性质的共识较少。可以在两个层次上探讨概念的纠缠-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数据与信息: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信息是有组织的或结构化的数据。该处理为特定目的或上下文提供了数据相关性,从而使其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有用和相关。换句话说,根据对个人、社区或任务具有意义和相关性的架构来构造数据,可以赋予意义或意义的潜能。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信息系统和我们脑海中的所有数据在收集或存放后都会具有一定的结构。信息系统总是对任何数据元素进行编码,以将其放置在数据库中并定位以备后用。人们在收集数据时需要“理解”数据,以相对于其他信息进行存储。因此,如果结构将数据与信息区分开,则我们会将信息存储在我们的思想和信息系统中。另一方面,例如,数据库中的数据项对特定的个人、团队或组织是否具有任何意义,取决于数据结构与个人、团队或组织的认知模式之间的一致性。那些认为信息存在于接收者心中的人在暗示,意义而非结构是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区别。这将导致这样的立场,即信息系统中可以保留的全部是数据。 信息与知识: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似乎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困惑。通常建议将信息处理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且适合于特定目的的数据。然而,知识被描述为“可操作的信息”,或与理解和能力相结合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意义是信息定义的核心,因此理解必须是实现意义的必要条件,因此似乎很难将行动能力或理解作为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区分者。此外,显性知识和信息之间的区别甚至更不可辩驳。如果知识是人的财产,并且体现了先验的理解、经验和学习,则很难争辩记录在文件和信息系统中的显性知识多于信息或少于信息。
六、结论本文通过检查信息系统和知识管理的许多最新教科书中的层次结构,重新审视了DIKW层次结构(在此称为智慧层次结构)。通过这一过程,它试图评估在以下方面是否存在明确的共识: 在所有书籍和资料中对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定义中都隐含了层次结构。通常,信息是根据数据定义的,知识是根据信息定义的,而智慧是根据知识定义的。但是,在将层次结构中较低元素转换为较高元素过程的描述中,一致性较少,因此缺乏定义的清晰度。我们特别建议: 此外,尽管处于DIKW层次结构的顶层,但智慧是知识管理和信息系统文献中被忽略的概念。如果信息系统和知识管理计划的目的是为适当的个人和组织行为和行为提供基础,那么更多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就需要进行有关个人和组织智慧本质的辩论。本文旨在引发和促进有关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知识管理学科的基本概念的辩论。如果它能促进关于以下方面的进一步辩论,它将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R.L.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6 (1989) 3–9
[2]Jennifer Rowley,The wisdom hierarch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KW hierarchy,2007,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63-180,Vol 33(2), doi: 10.1177/0165551506070706
[3] H. Cleveland, Information as a resource, The Futurist (December1982) 34–9.
[4] M. Zeleny,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s: towards integra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7(1) (1987) 59–70
[5]M. Cooley, Architecture or Bee? (Hogarth Press, London, 1987).
[6]G. Bellinger, D. Castro and A. Mills,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2004). Available at: www.systems-thinking.org/dikw/dikw.htm (accessed: 5 February 2006)
[7] D. Chaffey and S. Wood, Bus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mproving Performance U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FT Prentice Hall, Harlow, 2005).
[8] K.E. Pearlson and C.S Saunders, Managi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 Strategic Approach (Wiley, New York, 2004).
[9] A. Jashapara, Knowledge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T Prentice Hall, Harlow, 2005).
[10] C.W. Choo, The Knowing Organization: How Organisations Use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 Meaning, Create Knowledge, and Make Decisions (OUP , Oxford,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