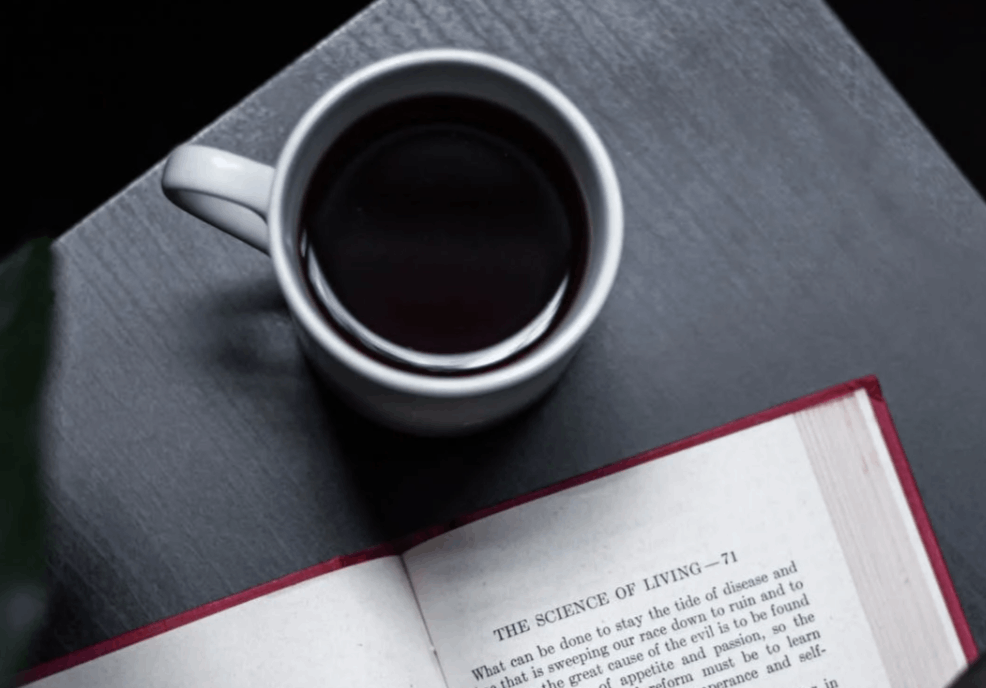【摘 要】 非常大的空间数据集的空间统计具有挑战性。数据集的大小 n n n n n n 通过使用一组固定数量的基函数,可以定义一个灵活的非平稳协方差函数族 ,这产生了我们称为 “固定秩克里金法” 的空间预测方法。具体来说,固定秩克里金法就是此类非平稳协方差函数支撑下的克里金法。当 n n n n n n
【原 文】 Cressie, N. and Johannesson, G. (2008) ‘Fixed rank kriging for very large spatial data sets: Fixed Rank Krig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70(1), pp. 209–22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11/j.1467-9868.2007.00633.x .
1 引言
克里金法或空间最佳线性无偏预测 (BLUP) 在地球和环境科学中非常流行,有时被称为最佳插值。 Matheron (1962)[26] [6] [7] n n n n × n n \times n n × n Σ \boldsymbol{\Sigma} Σ n n n O ( n 3 ) \mathcal{O}(n^3) O ( n 3 )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本文的目标是开发将克里金法的计算成本降低到 O ( n ) \mathcal{O}(n) O ( n )
(1)移动窗口法和稀疏化法方法
即使是几千数量级的空间数据集也会导致计算速度减慢,因此:
移动窗口方法 :数据子集方法由 Haas (1995) [13] 协方差矩阵稀疏化 :当协方差函数的变程有限时,协方差矩阵 Σ \boldsymbol{\Sigma} Σ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精度矩阵稀疏化 :Rue 和 Tjelmeland (2002) [33]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2)局部克里金方法
当数据集很大(数万量级)到非常大(数十万量级)时,直接克里金法可能会失效,通常会使用局部克里金邻域(例如 Cressie (1993) [7] 根据正交基给出等效表示然后采取截断基的形式 、 协方差锥化 、 近似迭代方法(如共轭梯度) 、 使用归纳变量实现稀疏近似 或 用更小的空间内填充位置集替换数据位置 。
最近研究的一个途径是近似克里金方程(Nychka 等,1996 年 [30] [31] [29] [2] [3] [12] [32] [23]
(3)多分辨率克里金法
另一种方法是选择协方差函数的类别,即使空间数据集很大,也可以对其进行精确的克里金法(例如 Huang 等 (2002) [18] [19] [21] [19] 10 8 10^8 1 0 8 3 3 3 n = 160000 n=160 000 n = 160000
(4)本文途径
上面提到的多分辨率模型隐含的空间协方差是 “非平稳的” 和 “块状的” 的。而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最佳空间预测的量级加速,该方法既可以使用非常灵活的协方差函数,也可以选择是否平滑,这取决于通过空间数据所展示的空间依赖类型(与 Tzeng 等(2005)[38] O ( n ) \mathcal{O}(n) O ( n )
我们将考虑一类 n × n n \times n n × n Σ \boldsymbol{\Sigma} Σ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r × r r \times r r × r r r r 第 4 节中给出的臭氧 (TCO) 数据应用中,n n n 173405 173 405 173405 r r r 396 396 396 第 2.3 节 中,我们给出了该方法的计算复杂度为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此外, 假设数据集是覆盖全球的卫星遥感数据,那么数据中的任何空间依赖性几乎肯定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异质性 。
本文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同时解决了 “数据集大小” 和 “空间异质性” 这两个问题。研究成果是我们称之为固定秩克里金法 (FRK) 的空间 BLUP 过程,它依赖于对 r r r n n n r × r r \times r r × r
为了完整起见,我们提到了另一种基于平滑样条的空间预测方法。与克里金法相比,平滑样条不依赖于空间随机过程(其协方差函数必须建模、拟合并用于计算最佳预测变量),但有结点(knots)和平滑(smoothing)等参数需要确定,而且空间数据集大小也会导致计算困难。Hastie (1996) [14] [20]
(5)本文贡献
(1) 在协方差结构建模方面 :要进行 FRK,必须指定(非平稳)协方差函数的形式;我们提出了一类足够灵活、可以对多个尺度的空间变化进行建模的协方差函数,它能够产生 n × n n \times n n × n Σ \boldsymbol{\Sigma} Σ
(2) 在空间预测方面 :最小化均方预测误差的空间 BLUP 在各种矩阵计算中涉及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n n n O ( n 3 ) \mathcal{O}(n^3) O ( n 3 )
本文结构如下:
第 2 节 介绍了克里金法并给出了定义 FRK 的方程。在第 3 节中,研究了 FRK 中使用的一类非平稳协方差函数,包括如何找到最适合数据的协方差函数。
第 4 节将该方法应用于 TCO 数据,其中 n = 173405 n = 173 405 n = 173405 n × n n \times n n × n 第 5 节包含讨论和结论,后面是技术附录 A。
2 Kriging:最优线性空间预测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克里金法的表示法,并将其等同于空间设置中的 BLUP。当空间数据集很大时,通常不可能精确计算克里金法。在本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展示了选择特定类别的非平稳空间协方差如何允许快速计算克里金预测变量(即空间 BLUP)和克里金标准差(即均方根预测误差)。
2.1 克里金方程
设 Y ( s ) : s ∈ D ⊂ R d } Y(\mathbf{s}) : \mathbf{s} \in \mathcal{D} \subset \mathbb{R}^d\} Y ( s ) : s ∈ D ⊂ R d } Y Y Y Z ( ⋅ ) Z(\cdot) Z ( ⋅ )
Z ( s ) ≡ Y ( s ) + ε ( s ) , s ∈ D (2.1) Z(\mathbf{s}) \equiv Y(\mathbf{s}) + \varepsilon(\mathbf{s}), \mathbf{s} \in \mathcal{D} \tag{2.1}
Z ( s ) ≡ Y ( s ) + ε ( s ) , s ∈ D ( 2.1 )
其中 { ε ( s ) : s ∈ D } \{\varepsilon(\mathbf{s}) : \mathbf{s} \in \mathcal{D} \} { ε ( s ) : s ∈ D } var ε ( s ) = σ 2 v ( s ) ∈ ( 0 , ∞ ) \operatorname{var}{\varepsilon(\mathbf{s})} = \sigma^2 v(\mathbf{s}) \in (0, \infty) var ε ( s ) = σ 2 v ( s ) ∈ ( 0 , ∞ ) s ∈ D \mathbf{s} \in \mathcal{D} s ∈ D σ 2 > 0 \sigma^2 > 0 σ 2 > 0 v ( ⋅ ) v(\cdot) v ( ⋅ ) Z ( ⋅ ) Z(\cdot) Z ( ⋅ ) { s 1 , … , s n } \{\mathbf{s}_1,\ldots ,\mathbf{s}_n\} { s 1 , … , s n }
Z ≡ ( Z ( s 1 ) , … , Z ( s n ) ) ′ (2.2) \mathbf{Z} \equiv (Z(\mathbf{s}_1),\dots,Z(\mathbf{s}_n))^{\prime} \tag{2.2}
Z ≡ ( Z ( s 1 ) , … , Z ( s n ) ) ′ ( 2.2 )
假设隐过程 Y ( ⋅ ) Y(\cdot) Y ( ⋅ )
Y ( s ) = t ( s ) ′ α + ν ( s ) , s ∈ D (2.3) Y(\mathbf{s}) = \mathbf{t}(\mathbf{s})^{\prime} \boldsymbol{\alpha} + ν(\mathbf{s}), \qquad \mathbf{s} \in \mathcal{D} \tag{2.3}
Y ( s ) = t ( s ) ′ α + ν ( s ) , s ∈ D ( 2.3 )
其中 t ( ⋅ ) ≡ ( t 1 ( ⋅ ) , … , t p ( ⋅ ) ) ′ \mathbf{t}(\cdot) \equiv (\mathbf{t}_1(\cdot),\ldots ,\mathbf{t}_p(\cdot))^{\prime} t ( ⋅ ) ≡ ( t 1 ( ⋅ ) , … , t p ( ⋅ ) ) ′ α ≡ ( α 1 , … , α p ) ′ \boldsymbol{\alpha} \equiv (\alpha_1,\ldots ,\alpha_p)^{\prime} α ≡ ( α 1 , … , α p ) ′ ν ( ⋅ ) ν(\cdot) ν ( ⋅ ) 0 < var { ν ( s ) } < ∞ 0 < \operatorname{var}\{ν(\mathbf{s})\} < \infty 0 < var { ν ( s )} < ∞ s ∈ D \mathbf{s} \in \mathcal{D} s ∈ D
cov { ν ( u ) , ν ( v ) } ≡ C ( u , v ) , u , v ∈ D (2.4) \operatorname{cov}\{ν(\mathbf{u}), ν(\mathbf{v})\} \equiv C(\mathbf{u,v}),\qquad \mathbf{u, v} \in \mathcal{D} \tag{2.4}
cov { ν ( u ) , ν ( v )} ≡ C ( u , v ) , u , v ∈ D ( 2.4 )
暂时未指定其矩。
如果我们用类似于 Z Z Z ε \boldsymbol{\varepsilon} ε Y \mathbf{Y} Y ν \boldsymbol{ν} ν 式(2.1) – 式(2.4) 表示了一个通用的线性混合模型,
Z = T α + δ , δ = ν + ε (2.5) \mathbf{Z} = \mathbf{T} \boldsymbol{\alpha} + \boldsymbol{\delta}, \qquad \boldsymbol{δ = ν + \varepsilon} \tag{2.5}
Z = T α + δ , δ = ν + ε ( 2.5 )
其中 T \mathbf{T} T ( t ( s 1 ) , … , t ( s n ) ) ′ (\mathbf{t}(\mathbf{s}_1),\ldots ,\mathbf{t}(\mathbf{s}_n))^{\prime} ( t ( s 1 ) , … , t ( s n ) ) ′ n × p n \times p n × p 式(2.5),误差项 δ \boldsymbol{\delta} δ E ( δ ) = 0 \mathbb{E}(\boldsymbol{\delta}) = 0 E ( δ ) = 0 var ( δ ) = Σ ≡ ( σ i j ) \operatorname{var}(\boldsymbol{\delta}) = \boldsymbol{\Sigma} \equiv (σ_{ij}) var ( δ ) = Σ ≡ ( σ ij )
σ i j = { C ( s j , s j ) + σ 2 v ( s j ) , i = j , C ( s i , s j ) , i ≠ j \sigma_{ij} = \begin{cases}
C(\mathbf{s}_j,\mathbf{s}_j) + \sigma^2 v(\mathbf{s}_j), &i = j,\\
C(\mathbf{s}_i,\mathbf{s}_j), &i \neq j
\end{cases}
σ ij = { C ( s j , s j ) + σ 2 v ( s j ) , C ( s i , s j ) , i = j , i = j
如果记 C ≡ ( C ( s i , s j ) ) \mathbf{C} \equiv (C(\mathbf{s}_i,\mathbf{s}_j)) C ≡ ( C ( s i , s j )) V ≡ diag { v ( s 1 ) , … , v ( s n ) } \mathbf{V} \equiv \operatorname{diag}\{v(\mathbf{s}_1),\ldots,v(\mathbf{s}_n)\} V ≡ diag { v ( s 1 ) , … , v ( s n )}
Σ = C + σ 2 V (2.6) \boldsymbol{\Sigma} = \mathbf{C} + \sigma^2 \mathbf{V} \tag{2.6}
Σ = C + σ 2 V ( 2.6 )
注意:这里没有假设协方差函数的平稳性或各向同性。
我们感兴趣对 Y Y Y Z Z Z s 0 \mathbf{s}_0 s 0 Y Y Y s 0 ∈ D \mathbf{s}_0 \in \mathcal{D} s 0 ∈ D s 0 \mathbf{s}_0 s 0 [7] 第 3.4.5 节 给出了新位置点处过程值 Y ( s 0 ) Y(\mathbf{s}_0) Y ( s 0 ) 克里金预测公式 :
Y ^ ( s 0 ) = t ( s 0 ) ′ α ^ + k ( s 0 ) ′ ( Z − T α ^ ) (2.7) \hat{Y}(\mathbf{s}_0) = \mathbf{t}(\mathbf{s}_0)^{\prime} \hat{\boldsymbol{\alpha}} + \mathbf{k}(\mathbf{s}_0)^{\prime}(\mathbf{Z} − \mathbf{T} \hat{\boldsymbol{\alpha}}) \tag{2.7}
Y ^ ( s 0 ) = t ( s 0 ) ′ α ^ + k ( s 0 ) ′ ( Z − T α ^ ) ( 2.7 )
其中,回归系数的估计为:
α ^ = ( T ′ Σ − 1 T ) − 1 T ′ Σ − 1 Z (2.8) \hat{\boldsymbol{\alpha}} = \mathbf{(T^{\prime} \boldsymbol{\Sigma}^{-1} T)^{-1} T^{\prime} \boldsymbol{\Sigma}^{-1}Z} \tag{2.8}
α ^ = ( T ′ Σ − 1 T ) − 1 T ′ Σ − 1 Z ( 2.8 )
k ( s 0 ) ′ = c ( s 0 ) ′ Σ − 1 (2.9) \mathbf{k(\mathbf{s}_0)^{\prime} = c(\mathbf{s}_0)^{\prime} \boldsymbol{\Sigma}^{-1}} \tag{2.9}
k ( s 0 ) ′ = c ( s 0 ) ′ Σ − 1 ( 2.9 )
其中,c ( s 0 ) ≡ ( C ( s 0 , s 1 ) , … , C ( s 0 , s n ) ) ′ \mathbf{c}(\mathbf{s}_0) \equiv (C(\mathbf{s}_0, \mathbf{s}_1),\ldots,C(\mathbf{s}_0, \mathbf{s}_n))^{\prime} c ( s 0 ) ≡ ( C ( s 0 , s 1 ) , … , C ( s 0 , s n ) ) ′ s 0 \mathbf{s_0} s 0
式(2.7) 与克里金法的等价性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因为克里金法的传统推导是根据变异函数得出的,并且没有测量误差(即 式(2.1) 中的 ε \varepsilon ε 0 0 0 [22] 第五章。 克里金预测标准差 为 Y ^ ( s 0 ) \hat{Y}(\mathbf{s}_0) Y ^ ( s 0 ) [ E { Y ( s 0 ) − Y ^ ( s 0 ) } 2 ] 1 / 2 [\mathbb{E}\{Y(\mathbf{s}_0) − \hat{Y}(\mathbf{s}_0)\}^2]^{1/2} [ E { Y ( s 0 ) − Y ^ ( s 0 ) } 2 ] 1/2
σ k ( s 0 ) = { C ( s 0 , s 0 ) − k ( s 0 ) ′ Σ k ( s 0 ) + ( t ( s 0 ) − T ′ k ( s 0 ) ) ′ ( T ′ Σ − 1 T ) − 1 ( t ( s 0 ) − T ′ k ( s 0 ) ) } 1 / 2 (2.10) \sigma_k(\mathbf{s}_0) = \{C(\mathbf{s}_0, \mathbf{s}_0) − \mathbf{k}(\mathbf{s}_0)^{\prime} \boldsymbol{\Sigma} \mathbf{k}(\mathbf{s}_0) + (\mathbf{t}(\mathbf{s}_0) − \mathbf{T}^{\prime} \mathbf{k}(\mathbf{s}_0))^{\prime} (\mathbf{T}^{\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T})^{-1}(\mathbf{t}(\mathbf{s}_0) − \mathbf{T}^{\prime} \mathbf{k}(\mathbf{s}_0)) \}^{1/2} \tag{2.10}
σ k ( s 0 ) = { C ( s 0 , s 0 ) − k ( s 0 ) ′ Σ k ( s 0 ) + ( t ( s 0 ) − T ′ k ( s 0 ) ) ′ ( T ′ Σ − 1 T ) − 1 ( t ( s 0 ) − T ′ k ( s 0 )) } 1/2 ( 2.10 )
当 式(2.7) 和 式(2.10) 中的预测位置 s 0 \mathbf{s}_0 s 0 D \mathcal{D} D D \mathcal{D} D
仔细观察 式(2.7) 和 式(2.10),可以发现协方差矩阵的求逆运算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n × n n \times n n × n O ( n 3 ) \mathcal{O}(n^3) O ( n 3 ) n n n 式(2.7) 和 式(2.10) 通常无法在任何可接受的时间内完成计算。
在下一小节中,我们将展示如何通过选择协方差函数类,来加速最佳空间预测(即克里金法)。
2.2 空间协方差函数
一般而言, 式(2.4) 定义的协方差函数 C ( u , v ) C(\mathbf{u,v}) C ( u , v ) R d × R d \mathbb{R}^d \times \mathbb{R}^d R d × R d C ( u , v ) C(\mathbf{u,v}) C ( u , v ) C C C u − v \mathbf{u-v} u − v
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通过 r r r 式 2.11):
S ( u ) ≡ ( S 1 ( u ) , … , S r ( u ) ) ′ , u ∈ R d (2.11) \mathbf{S(\mathbf{u})} \equiv (S_1(\mathbf{u}),\ldots,S_r(\mathbf{u}))^{\prime}, \qquad \mathbf{u} \in \mathbb{R}^d \tag{2.11}
S ( u ) ≡ ( S 1 ( u ) , … , S r ( u ) ) ′ , u ∈ R d ( 2.11 )
式中的 r r r 在 3.1 节 中给出。如果令 K \mathbf{K} K r × r r \times r r × r cov { Y ( u ) , Y ( v ) } \operatorname{cov} \{ Y(\mathbf{u}), Y(\mathbf{v}) \} cov { Y ( u ) , Y ( v )}
C ( u , v ) = S ( u ) ′ K S ( v ) , u , v ∈ R d (2.12) C(\mathbf{u,v}) = \mathbf{S}(\mathbf{u})^{\prime} \mathbf{KS}(\mathbf{v}), \qquad \mathbf{u, v} \in \mathbb{R}^d \tag{2.12}
C ( u , v ) = S ( u ) ′ KS ( v ) , u , v ∈ R d ( 2.12 )
上式已被证明是一个非负定函数(第 3.1 节),因此是有效的协方差函数(Cressie 和 Johannesson,2006 年 [8] τ 2 I ( u = v ) \tau^2 \mathbb{I}(\mathbf{u=v}) τ 2 I ( u = v ) 式(2.12) 中,不过我们在本文中没有这样做;见第 5 节。
很容易看出, 式 (2.12) 是将空间过程 ν ( s ) ν(\mathbf{s}) ν ( s ) ν ( s ) = S ( s ) ′ η ν(\mathbf{s})= \mathbf{S}(\mathbf{s})^{\prime} \boldsymbol{\eta} ν ( s ) = S ( s ) ′ η s ∈ D \mathbf{s} \in \mathcal{D} s ∈ D η \boldsymbol{\eta} η r r r cov ( η ) = K \operatorname{cov}(\boldsymbol{\eta}) = \mathbf{K} cov ( η ) = K ν ( ⋅ ) ν(\cdot) ν ( ⋅ ) 空间随机效应 。 因此,式(2.3) 中的模型 Y ( s ) = t ( s ) ′ β + S ( s ) ′ η Y(\mathbf{s}) = \mathbf{t}(\mathbf{s})^{\prime} \boldsymbol{\beta} + \mathbf{S}(\mathbf{s})^{\prime} \boldsymbol{\eta} Y ( s ) = t ( s ) ′ β + S ( s ) ′ η 空间混合效应模型 。
2.3 固定秩克里金法
(1)训练点的协方差矩阵
由 式(2.12) 可得 Y \mathbf{Y} Y ν \boldsymbol{ν} ν n × n n \times n n × n C = S K S ′ \mathbf{C=SKS^{\prime}} C = SK S ′
Σ = S K S ′ + σ 2 V (2.13) \boldsymbol{\Sigma} = \mathbf{SKS^{\prime}} + \sigma^2 \mathbf{V} \tag{2.13}
Σ = SK S ′ + σ 2 V ( 2.13 )
其中未知参数是正定的 r × r r \times r r × r K \mathbf{K} K σ 2 > 0 \sigma^2 > 0 σ 2 > 0 S \mathbf{S} S n × r n \times r n × r ( i , l ) (i,l) ( i , l ) i i i l l l S l ( s i ) S_l(\mathbf{s}_i) S l ( s i ) V \mathbf{V} V S \mathbf{S} S V \mathbf{V} V S \mathbf{S} S
(2)测试点的协方差
进一步地,与新位置 s 0 \mathbf{s_0} s 0
cov { Y ( s 0 ) , Z } = c ( s 0 ) ′ = S ( s 0 ) ′ K S ′ (2.14) \operatorname{cov} \{Y(\mathbf{s}_0), \mathbf{Z}\} = \mathbf{c(s_0)^{\prime}} = \mathbf{S(\mathbf{s}_0)^{\prime}KS^{\prime}} \tag{2.14}
cov { Y ( s 0 ) , Z } = c ( s 0 ) ′ = S ( s 0 ) ′ K S ′ ( 2.14 )
即在由 式(2.1) 、 式(2.3) 和 式(2.12) 指定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找到 式(2.7) 和 式(2.10) 中需要的所有分量的表达式。
(3)精度矩阵
当 n n n 式(2.12) 的协方差函数形式使得克里金预测方程中的计算仅涉及 r × r r \times r r × r 式(2.13),则协方差矩阵 Σ \boldsymbol{\Sigma} Σ
Σ − 1 = σ − 1 V − 1 / 2 { I + ( σ − 1 V − 1 / 2 S ) K ( σ − 1 V − 1 / 2 S ) ′ } − 1 σ − 1 V − 1 / 2 (2.15) \boldsymbol{\Sigma}^{-1} = \sigma^{-1} \mathbf{V}^{-1/2} \{\mathbf{I} + (\sigma^{−1} \mathbf{V}^{-1/2} \mathbf{S}) \mathbf{K} (\sigma^{-1} \mathbf{V}^{-1/2}\mathbf{S})^{\prime}\}^{-1} \sigma^{-1} \mathbf{V}^{-1/2} \tag{2.15}
Σ − 1 = σ − 1 V − 1/2 { I + ( σ − 1 V − 1/2 S ) K ( σ − 1 V − 1/2 S ) ′ } − 1 σ − 1 V − 1/2 ( 2.15 )
注意其中大括号内的项,具有 I + P K P ′ \mathbf{I + PKP^{\prime}} I + PK P ′ P \mathbf{P} P n × r n \times r n × r
让我们首先分析 I + P K P ′ \mathbf{I + PKP^{\prime}} I + PK P ′ 式 2.15。
根据 Sherman–Morrison–Woodbury 公式, I + P K P ′ \mathbf{I + PKP^{\prime}} I + PK P ′
I + P K P ′ = I + ( I + P K P ′ ) P K ( I + P ′ P K ) − 1 P ′ \mathbf{I + PKP^{\prime} = I + (I + PKP^{\prime})PK(I + P^{\prime}PK)^{−1}P^{\prime}}
I + PK P ′ = I + ( I + PK P ′ ) PK ( I + P ′ PK ) − 1 P ′
在公式两边乘以 ( I + P K P ′ ) − 1 \mathbf{(I + PKP^{\prime})^{-1}} ( I + PK P ′ ) − 1
( I + P K P ′ ) − 1 = I − P ( K − 1 + P ′ P ) − 1 P ′ \mathbf{(I + PKP^{\prime})^{-1} = I − P(\mathbf{K}^{-1} + P^{\prime}P)^{-1}P^{\prime}}
( I + PK P ′ ) − 1 = I − P ( K − 1 + P ′ P ) − 1 P ′
(注:此处为 Sherman–Morrison–Woodbury 公式所涵盖的结果,参见 Henderson 和 Searle (1981 [16]
将上式用于 式(2.15),可以得到如下精度矩阵的简化计算公式:
Σ − 1 = ( σ 2 V ) − 1 − ( σ 2 V ) − 1 S { K − 1 + S ′ ( σ 2 V ) − 1 S } − 1 S ′ ( σ 2 V ) − 1 (2.16) \boldsymbol{\Sigma}^{-1} = (\sigma^2 \mathbf{V})^{-1} − (\sigma^2 \mathbf{V})^{-1} \mathbf{S} \{\mathbf{K}^{-1} + \mathbf{S}^{\prime}(\sigma^2 \mathbf{V})^{-1} \mathbf{S}\}^{-1} \mathbf{S}^{\prime}(\sigma^2 \mathbf{V})^{-1} \tag{2.16}
Σ − 1 = ( σ 2 V ) − 1 − ( σ 2 V ) − 1 S { K − 1 + S ′ ( σ 2 V ) − 1 S } − 1 S ′ ( σ 2 V ) − 1 ( 2.16 )
请注意, 式(2.16) 中原始协方差矩阵的求逆运算仅涉及 r × r r \times r r × r K \mathbf{K} K n × n n \times n n × n V \mathbf{V} V r ≪ n r \ll n r ≪ n
(4)空间预测
最后, 式(2.7) 的克里金法预测器(空间 BLUP)可以改写为:
Y ^ ( s 0 ) = t ( s 0 ) ′ α ^ + S ( s 0 ) ′ K S ′ Σ − 1 ( Z − T α ^ ) (2.17) \hat{Y}(\mathbf{s}_0) = \mathbf{t}(\mathbf{s}_0)^{\prime} \hat{\boldsymbol{α}} + \mathbf{S}(\mathbf{s}_0)^{\prime} \mathbf{KS}^{\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Z} − \mathbf{T} \hat{\boldsymbol{\alpha}}) \tag{2.17}
Y ^ ( s 0 ) = t ( s 0 ) ′ α ^ + S ( s 0 ) ′ KS ′ Σ − 1 ( Z − T α ^ ) ( 2.17 )
其中 α ^ = ( T ′ Σ − 1 T ) − 1 T ′ Σ − 1 Z \hat{\boldsymbol{\alpha}} = (\mathbf{T}^{\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T})^{-1} \mathbf{T}^{\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Z} α ^ = ( T ′ Σ − 1 T ) − 1 T ′ Σ − 1 Z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式(2.16) 计算给出。
(5)预测方差
式(2.10) 的克里金标准差可以改写为:
σ k ( s 0 ) = { S ( s 0 ) ′ K S ( s 0 ) − S ( s 0 ) ′ K S ′ Σ − 1 S K S ( s 0 ) + ( t ( s 0 ) − T ′ Σ − 1 S K S ( s 0 ) ) ′ ( T ′ Σ − 1 T ) − 1 ( t ( s 0 ) − T ′ Σ − 1 S K S ( s 0 ) ) } 1 / 2 (2.18) \begin{align*}
\sigma_k(\mathbf{s}_0) = \{ &\mathbf{S}(\mathbf{s}_0)^{\prime} \mathbf{KS(s_0)} − \mathbf{S(s_0)}^{\prime} \mathbf{KS}^{\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SK S(s_0)} \\
&+ ( \mathbf{\mathbf{t}(s_0) − T^{\prime} \boldsymbol{\Sigma}^{-1} SK S(\mathbf{s}_0)})^{\prime} ( \mathbf{T^{\prime} \boldsymbol{\Sigma}^{-1} T})^{-1} (\mathbf{\mathbf{t}(s_0) − T^{\prime} \boldsymbol{\Sigma}^{-1} SK S(s_0)}) \}^{1/2}
\end{align*} \tag{2.18}
σ k ( s 0 ) = { S ( s 0 ) ′ KS ( s 0 ) − S ( s 0 ) ′ KS ′ Σ − 1 SKS ( s 0 ) + ( t ( s 0 ) − T ′ Σ − 1 SKS ( s 0 ) ) ′ ( T ′ Σ − 1 T ) − 1 ( t ( s 0 ) − T ′ Σ − 1 SKS ( s 0 ) ) } 1/2 ( 2.18 )
其中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式(2.16) 给出。
固定秩克里金法(Fixed Rank Kriging, FRK) 是 式(2.16) – 式(2.18) 方法的总称(Cressie 和 Johannesson,2006 [8] 式(2.17) 和 式(2.18) 中的预测位置 s 0 \mathbf{s}_0 s 0 D \mathcal{D} D
(4)计算复杂度分析
仔细分析 式(2.16) – 式(2.18),对于固定的回归变量数量 p p p K \mathbf{K} K r r r 式(2.12) 定义的协方差模型中,FRK 的计算负担仅关于 n n n σ 2 V = I \sigma^2 \mathbf{V} = \mathbf{I} σ 2 V = I
与 式(2.17) 和 式(2.18) 相关的计算涉及 S ′ Σ − 1 S \mathbf{S}^{\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S} S ′ Σ − 1 S S ′ Σ − 1 a \mathbf{S}^{\prime} \boldsymbol{\Sigma}^{-1} \mathbf{a} S ′ Σ − 1 a Σ − 1 a \boldsymbol{\Sigma}^{-1} \mathbf{a} Σ − 1 a a \mathbf{a} a n n n
为了执行上述计算,可以预计算 A ≡ S ′ S \mathbf{A} \equiv \mathbf{S}^{\prime} \mathbf{S} A ≡ S ′ S B ≡ ( K − 1 + S ′ S ) 1 / 2 \mathbf{B} \equiv (\mathbf{K}^{-1} + \mathbf{S^{\prime}S})^{1/2} B ≡ ( K − 1 + S ′ S ) 1/2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n > r n > r n > r
由 式(2.16) 可知,S ′ Σ − 1 S = A − A B A \mathbf{S^{\prime} \boldsymbol{\Sigma}^{-1} S = A − ABA} S ′ Σ − 1 S = A − ABA A B A \mathbf{ABA} ABA O ( r 3 ) \mathcal{O}(r^3) O ( r 3 )
S ′ Σ − 1 a \mathbf{S^{\prime} \boldsymbol{\Sigma}^{-1}a} S ′ Σ − 1 a Σ − 1 a \boldsymbol{\Sigma}^{-1} \mathbf{a} Σ − 1 a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式(2.17) 的预测方程计算成本为 O ( r ) \mathcal{O}(r) O ( r ) 对于固定的 s 0 \mathbf{s}_0 s 0 式(2.18) 的预测方差计算成本为 O ( r 2 ) \mathcal{O}(r^2) O ( r 2 ) p ≪ r p \ll r p ≪ r
因此,预测的总计算规模为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正如 第 4 节 所证实的那样,FRK 方法使得构建基于非常大的空间数据集的克里金预测变量图和克里金标准差图成为可能。
克里金方法和平滑方法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参见如 Cressie (1993 [7] 第 5.9 节 和 Nychka (2000 [29] 式(2.12) 的 FRK 是由固定秩平滑技术所驱动的,该技术从正则化和岭回归演化而来(Johannesson 和 Cressie,2004b [20] 固定秩正定矩阵 K K K 基函数 { S l ( ⋅ ) } \{S_l(\cdot)\} { S l ( ⋅ )} 式 2.12 形式的空间协方差函数,进而产生高计算效率的克里金预测和克里金标准差。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详细考虑 K \mathbf{K} K σ 2 \sigma^2 σ 2
3 协方差函数的选择
在本文中考虑的协方差函数族,需要满足如下基函数表达形式:
C ( u , v ) = S ( u ) ′ K S ( v ) , u , v ∈ R d C(\mathbf{u,v}) = \mathbf{S(\mathbf{u})^{\prime} K S(\mathbf{v})}, \qquad \mathbf{u, v} \in \mathbb{R}^d
C ( u , v ) = S ( u ) ′ KS ( v ) , u , v ∈ R d
其中 K \mathbf{K} K r × r r \times r r × r S ( ⋅ ) \mathbf{S}(\cdot) S ( ⋅ ) S 1 ( ⋅ ) , … , S r ( ⋅ ) S_1(\cdot),\ldots ,S_r(\cdot) S 1 ( ⋅ ) , … , S r ( ⋅ ) r × 1 r \times 1 r × 1 r r r
上述表示形式类似于 Stroud 等 (2001 [37] Σ \boldsymbol{\Sigma} Σ
下面我们将给出此类协方差函数的一些性质。在经典地统计学意义上,我们还将展示数据是如何被二次使用(例如 Cressie (1989),注:此处指参数估计和空间预测两个过程都需要观测数据的参与):它们不仅(线性地)存在于克里金预测器( 式(2.7))中;还可(非线性地)被用于估计空间协方差参数 K \mathbf{K} K σ 2 \sigma^2 σ 2
3.1 基本性质
(1)协方差函数的非负定性
最重要的性质是:函数 C ( u , v ) C(\mathbf{u,v}) C ( u , v ) R d \mathbb{R}^d R d { s i : i = 1 , … , m } \{\mathbf{s}_i : i = 1,\ldots ,m\} { s i : i = 1 , … , m } { b i : i = 1 , … , m } \{b_i : i = 1,\ldots ,m \} { b i : i = 1 , … , m } m m m K \mathbf{K} K
∑ i = 1 m ∑ j = 1 m b i b j C ( s i , s j ) = b m ′ ( S m K S m ′ ) b m = ( S m ′ b m ) ′ K ( S m ′ b m ) ≥ 0 \sum^{m}_{i=1} \sum^{m}_{j=1} b_i b_j C(\mathbf{s}_i,\mathbf{s}_j) = \mathbf{b^{\prime}_m (S_m K S^{\prime}_m)b_m} = \mathbf{(S^{\prime}_m b_m)^{\prime} K (S^{\prime}_mb_m)} \geq 0
i = 1 ∑ m j = 1 ∑ m b i b j C ( s i , s j ) = b m ′ ( S m K S m ′ ) b m = ( S m ′ b m ) ′ K ( S m ′ b m ) ≥ 0
(2)与 KL 展开的关系
一个与 式(2.12) 相关但不同的模型是 Karhunen–Loéve 展开(例如 Adler (1981 [1] 第 3.3 节)。
注:
KL 展开 : 将一个随机变量展开为多个随机系数与正交基函数的线性组合,即: y ( s ) = ∑ i m λ i ϕ i ( s ) y(\mathbf{s}) = \sum^m_i \lambda_i \phi_i(\mathbf{s}) y ( s ) = ∑ i m λ i ϕ i ( s ) ϕ i ( s ) \phi_i(\mathbf{s}) ϕ i ( s ) λ i \lambda_i λ i
根据 KL 展开,可以将随机过程的协方差函数改写为:
C 1 ( u , v ) ≡ ∑ l = 1 ∞ λ l ϕ l ( u ) ϕ l ( v ) (3.1) C_1(\mathbf{u,v}) \equiv \sum^{\infty}_{l=1} λ_l \phi_l(\mathbf{u}) \phi_l(\mathbf{v}) \tag{3.1}
C 1 ( u , v ) ≡ l = 1 ∑ ∞ λ l ϕ l ( u ) ϕ l ( v ) ( 3.1 )
其中 { λ l } \{λ_l\} { λ l } { ϕ l ( ⋅ ) } \{\phi_l(\cdot)\} { ϕ l ( ⋅ )}
∫ C 1 ( u , v ) ϕ ( v ) d v = λ ϕ ( u ) \int C_1(\mathbf{u,v}) \phi(\mathbf{v}) d \mathbf{v} = λ \phi(\mathbf{u})
∫ C 1 ( u , v ) ϕ ( v ) d v = λ ϕ ( u )
如果将 式(3.1) 在第 k k k
C 2 ( u , v ) = ∑ l = 1 k λ l ϕ l ( u ) ϕ l ( v ) ≡ ϕ ( u ) ′ Λ ϕ ( v ) C_2(\mathbf{u,v}) = \sum^{k}_{l=1} λ_l \phi_l(\mathbf{u}) \phi_l(\mathbf{v}) \equiv \boldsymbol{\phi(\mathbf{u})^{\prime} \Lambda \phi(\mathbf{v})}
C 2 ( u , v ) = l = 1 ∑ k λ l ϕ l ( u ) ϕ l ( v ) ≡ ϕ ( u ) ′ Λ ϕ ( v )
上式最右侧为矩阵-向量表示,其中 Λ \boldsymbol{\Lambda} Λ k × k k \times k k × k
不失一般性:
假设截断只保留具有正特征值的项;那么截断后的 Karhunen–Loéve 展开显然是 式(2.12) 的一个特例。
反之,如果将 式(2.12) 中的 K \mathbf{K} K K = P Λ P ′ \mathbf{K = P \boldsymbol{\Lambda} P^{\prime}} K = P Λ P ′ C ( u , v ) = ( P ′ S ( u ) ) ′ Λ ( P ′ S ( v ) ) C(\mathbf{u,v}) = \mathbf{(P^{\prime} S(u))^{\prime} \boldsymbol{\Lambda} (P^{\prime} S(v))} C ( u , v ) = ( P ′ S ( u ) ) ′ Λ ( P ′ S ( v )) { ϕ l ( ⋅ ) } \{\phi_l(\cdot)\} { ϕ l ( ⋅ )}
综上所述,实现 式(2.12) 的模型需要做如下工作:
(1)选择一组有限的(可能非正交的)基函数 ϕ ( s ) \boldsymbol{\phi}(\mathbf{s}) ϕ ( s ) 第 3.2 节。
(2)估计一个固定秩的协方差矩阵 K \mathbf{K} K I \mathbf{I} I 第 3.3 节;
3.2 基函数的选择
(1)基函数的可选范围
固定秩的协方差矩阵 K \mathbf{K} K S ( ⋅ ) ≡ ( S 1 ( ⋅ ) , … , S n ( ⋅ ) ) ′ \mathbf{S}(\cdot) \equiv (S_1(\cdot),\ldots ,S_n(\cdot))^{\prime} S ( ⋅ ) ≡ ( S 1 ( ⋅ ) , … , S n ( ⋅ ) ) ′ S 1 ( ⋅ ) , … , S r ( ⋅ ) S_1(\cdot),\ldots ,S_r(\cdot) S 1 ( ⋅ ) , … , S r ( ⋅ ) [40] [39] [15]
Nychka (2000 [29] [31] r = n r = n r = n r r r r r r K \mathbf{K} K [31] 式(2.12) 协方差模型的固定秩基函数分解形式,能够逼近地统计学中使用的其他协方差函数,例如各向同性的指数模型。事实上,在第 4 节中,我们将在地球上进行克里金法,而选择的基函数为多分辨率局部双平方函数。
(2)建议考虑多分辨率
在基函数选择方面,我们的主要建议是要考虑多分辨率,以使 式(2.12) 的协方差模型能够捕获多个尺度的可变性。
在 第 2.2 节 中,我们曾提到 式(2.12) 可以被等效地认为是空间随机效应模型 ν ( ⋅ ) = S ( ⋅ ) ′ η \nu(\cdot)=\mathbf{S}(\cdot)^{\prime} \boldsymbol{\eta} ν ( ⋅ ) = S ( ⋅ ) ′ η η \boldsymbol{\eta} η K \mathbf{K} K S ( ⋅ ) \mathbf{S}(\cdot) S ( ⋅ )
实际上, 式(2.3) 中的均值函数 t ( ⋅ ) ′ α \mathbf{t}(\cdot)^{\prime} \boldsymbol{\alpha} t ( ⋅ ) ′ α S ( ⋅ ) ′ η \mathbf{S}(\cdot)^{\prime} \boldsymbol{\eta} S ( ⋅ ) ′ η
最显著的多分辨率函数类别是各种类型的小波;同样,第 4 节 中使用的局部双平方函数类也是多分辨率的(但不正交)。事实上,在对气溶胶卫星数据的分析中,Shi 和 Cressie (2007 [35] W W W t ( ⋅ ) \mathbf{t}(\cdot) t ( ⋅ ) S ( ⋅ ) \mathbf{S}(\cdot) S ( ⋅ ) t ( ⋅ ) \mathbf{t}(\cdot) t ( ⋅ ) S ( ⋅ ) \mathbf{S}(\cdot) S ( ⋅ ) [35]
(3)小结
从多种基函数中选择哪一类基函数的问题尚在研究之中。但如果希望比较两个 FRK 图以检测变化异常,我们建议两者采用相同的 t ( ⋅ ) \mathbf{t}(\cdot) t ( ⋅ ) S ( ⋅ ) \mathbf{S}(\cdot) S ( ⋅ )
从计算角度来看,使用一类可以快速计算 S ′ V − 1 S \mathbf{S}^{\prime} \mathbf{V}^{-1} \mathbf{S} S ′ V − 1 S S ′ a \mathbf{S^{\prime}a} S ′ a a \mathbf{a} a 第 2.3 节中看到此类计算通常为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第 4 节中的双平方基或小波基以及稀疏矩阵库,计算成本实际上可以降低到 O ( k r 2 ) \mathcal{O}(kr^2) O ( k r 2 ) k < n k < n k < n
3.3 协方差函数的拟合
本文中拟合空间协方差函数的策略与经典地统计学方法一致,如 Matheron (1963 [27] [22]
首先,基于矩量法获得协方差矩阵的经验估计量 Σ ^ \hat{\boldsymbol{\Sigma}} Σ ^
然后,选择一个能够保证正定的参数化矩阵类 { Σ ( θ ) : θ ∈ Θ } \{\boldsymbol{\Sigma(\theta) : \theta} \in \Theta\} { Σ ( θ ) : θ ∈ Θ } Σ ^ \hat{\boldsymbol{\Sigma}} Σ ^ Σ ( θ ^ ) \boldsymbol{\Sigma(\hat{\theta})} Σ ( θ ^ ) θ ^ ∈ Θ \hat{\boldsymbol{\theta}} \in \Theta θ ^ ∈ Θ
最后,将 Σ ( θ ^ ) \boldsymbol{\Sigma(\hat{\theta})} Σ ( θ ^ ) 式(2.17) 和 式(2.18) 。
注: 在 Zammit-Mangion 等(2021)中,提出了对 FRK 的改进和基于 EM 算法的估计。见 “Zammit-Mangion, Andrew, and Noel Cressie. “FRK : An R Package for Spatial and Spatio-Temporal Prediction with Large Dataset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98, no. 4 (2021). https://doi.org/10.18637/jss.v098.i04” 。
在 FRK 中,参数 θ \boldsymbol{\theta} θ r × r r \times r r × r K \mathbf{K} K σ 2 ∈ ( 0 , ∞ ) \sigma^2 \in (0, \infty ) σ 2 ∈ ( 0 , ∞ ) K ^ \hat{\mathbf{K}} K ^ σ ^ 2 \hat{\sigma}^2 σ ^ 2
如果矩阵 B \mathbf{B} B A \mathbf{A} A B − A \mathbf{B−A} B − A
∥ A ∥ F = ∑ i = 2 m ∑ j = 1 n ∣ a i j ∣ 2 = trace ( A ∗ A ) = ∑ i = 1 min { m , n } σ i 2 \|A\|_{F}=\sqrt{\sum_{i=2}^{m} \sum_{j=1}^{n}\left|a_{i j}\right|^{2}}=\sqrt{\operatorname{trace}\left(A^{*} A\right)}=\sqrt{\sum_{i=1}^{\min \{m, n\}} \sigma_{i}^{2}}
∥ A ∥ F = i = 2 ∑ m j = 1 ∑ n ∣ a ij ∣ 2 = trace ( A ∗ A ) = i = 1 ∑ m i n { m , n } σ i 2
可以将矩阵看做一个由各列向量拼接起来的长向量,而 Frobenius 范数正是该向量的欧式模。
(1) 去除趋势分量
如果要定义方差和协方差的经验估计,首先需要去除观测数据中的趋势分量(即均值函数部分)。由于缺乏空间依赖性的初始知识,同时考虑到计算效率,我们使用 α \boldsymbol{\alpha} α
α ˉ ≡ ( T ′ T ) − 1 T ′ Z (3.2) \boldsymbol{\bar{\alpha}} \equiv \mathbf{(T^{\prime} T)^{-1} T^{\prime} Z} \tag{3.2}
α ˉ ≡ ( T ′ T ) − 1 T ′ Z ( 3.2 )
然后,计算细节残差:
D ( s i ) ≡ Z ( s i ) − t ( s i ) ′ α ˉ , i = 1 , … , n (3.3) D(\mathbf{s}_i) \equiv Z(\mathbf{s}_i) − \mathbf{t}(\mathbf{s}_i)^{\prime} \bar{\boldsymbol{\alpha}},\qquad i = 1,\ldots ,n \tag{3.3}
D ( s i ) ≡ Z ( s i ) − t ( s i ) ′ α ˉ , i = 1 , … , n ( 3.3 )
(2)协方差函数拟合
与经典地统计学一样,我们将数据 “装箱” 以计算空间依赖性的矩量法估计量。箱(bin)的数量 M M M r r r n n n
装箱后拟合的矩量法,常见于传统的克里金方法。其本质上就是拟合一条与箱均值最接近的协方差函数曲线。
假设 { u j : j = 1 , … , M } \{\mathbf{u}_j : j = 1,\ldots ,M\} { u j : j = 1 , … , M } r ≤ M < n r \leq M < n r ≤ M < n D \mathcal{D} D j j j u j \mathbf{u}_j u j N ( u j ) N(\mathbf{u}_j) N ( u j )
w j i ≡ { 1 , if s i ∈ N ( u j ) , 0 , otherwise. (3.4) w_{ji} \equiv \begin{cases}
1, & \text{ if } \mathbf{s}_i \in N(\mathbf{u}_j), \\
0,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tag{3.4}
w ji ≡ { 1 , 0 , if s i ∈ N ( u j ) , otherwise. ( 3.4 )
其中 i = 1 , … , n i = 1,\ldots ,n i = 1 , … , n j = 1 , … , M j = 1,\ldots ,M j = 1 , … , M
令 w j ≡ ( w j 1 , … , w j n ) ′ \mathbf{w}_j \equiv (w_{j1},\ldots ,w_{jn})^{\prime} w j ≡ ( w j 1 , … , w jn ) ′
Z j ˉ ≡ w j ′ ( Z − T α ˉ ) / w j ′ 1 n (3.5) \bar{Z_j} \equiv \mathbf{w}^{\prime}_j (\mathbf{Z} − \mathbf{T} \bar{\boldsymbol{\alpha}}) / \mathbf{w}^{\prime}_j \mathbf{1}_n \tag{3.5}
Z j ˉ ≡ w j ′ ( Z − T α ˉ ) / w j ′ 1 n ( 3.5 )
其中 1 n \mathbf{1}_n 1 n 1 1 1 n × 1 n \times 1 n × 1 u j , j = 1 , … , M \mathbf{u}_j, j = 1,\ldots ,M u j , j = 1 , … , M
在 附录 A 的近似 (A.4) 中,我们展示了 Σ M ≡ var ( Z 1 ˉ , … , Z M ˉ ) \boldsymbol{\Sigma}_M \equiv \operatorname{var}(\bar{Z_1},\ldots ,\bar{Z_M}) Σ M ≡ var ( Z 1 ˉ , … , Z M ˉ ) Σ ˉ M ( K , σ 2 ) ≡ S ˉ K S ˉ ′ + σ 2 V ˉ \bar{\boldsymbol{\Sigma}}_M(\mathbf{K}, \sigma^2) \equiv \bar{\mathbf{S}} \mathbf{K} \bar{\mathbf{S}}^{\prime} + \sigma^2 \bar{\mathbf{V}} Σ ˉ M ( K , σ 2 ) ≡ S ˉ K S ˉ ′ + σ 2 V ˉ S ˉ \bar{\mathbf{S}} S ˉ V ˉ \bar{\mathbf{V}} V ˉ S \mathbf{S} S V \mathbf{V} V 附录 A 的表达式 (A.2) 中,我们给出了基于细节残差 式(3.3) 的经验正定估计 Σ ^ M \hat{\boldsymbol{\Sigma}}_M Σ ^ M K \mathbf{K} K σ 2 ∈ ( 0 , ∞ ) \sigma^2 \in (0, \infty ) σ 2 ∈ ( 0 , ∞ ) Σ ˉ M ( K , σ 2 ) \bar{\boldsymbol{\Sigma}}_M(\mathbf{K}, \sigma^2) Σ ˉ M ( K , σ 2 ) Σ ^ M \hat{\boldsymbol{\Sigma}}_M Σ ^ M
同阶的两个矩阵 A \mathbf{A} A B \mathbf{B} B
∥ A − B ∥ 2 ≡ tr { ( A − B ) ′ ( A − B ) } = ∑ j , k ( A j k − B j k ) 2 (3.6) \|A − B\|^2 \equiv \operatorname{tr}\{(\mathbf{A − B})^{\prime}( \mathbf{A − B})\} = \sum_{j,k}(A_{jk} − B_{jk})^2 \tag{3.6}
∥ A − B ∥ 2 ≡ tr {( A − B ) ′ ( A − B )} = j , k ∑ ( A jk − B jk ) 2 ( 3.6 )
这也被 Hastie (1996 [14] [10] [4] 式(3.6) 的未加权版本。
当 σ 2 = 0 \sigma^2 = 0 σ 2 = 0 Σ ^ M ( K , 0 ) = S ˉ K S ˉ ′ \hat{\boldsymbol{\Sigma}}_M(\mathbf{K},0) = \mathbf{ \bar{S} K \bar{S}^{\prime}} Σ ^ M ( K , 0 ) = S ˉ K S ˉ ′ ∥ Σ ^ M − Σ ˉ M ( K , 0 ) ∥ \|\hat{\boldsymbol{\Sigma}}_M − \bar{\boldsymbol{\Sigma}}_M(\mathbf{K},0)\| ∥ Σ ^ M − Σ ˉ M ( K , 0 ) ∥ K \mathbf{K} K
K ^ = R − 1 Q ′ Σ ^ M Q ( R − 1 ) ′ (3.7) \mathbf{ \hat{K} = R^{−1} Q^{\prime} \hat{\boldsymbol{\Sigma}}_M Q (R^{−1})^{\prime}} \tag{3.7}
K ^ = R − 1 Q ′ Σ ^ M Q ( R − 1 ) ′ ( 3.7 )
对应的拟合协方差矩阵为 Σ ˉ M ( K ^ , 0 ) = Q Q ′ Σ ^ M Q Q ′ \bar{\boldsymbol{\Sigma}}_M ( \hat{\mathbf{K}} ,0) = \mathbf{QQ^{\prime} \hat{\boldsymbol{\Sigma}}_M QQ^{\prime}} Σ ˉ M ( K ^ , 0 ) = Q Q ′ Σ ^ M Q Q ′ S ˉ = Q R \mathbf{\bar{S} = QR} S ˉ = QR S ˉ \bar{\mathbf{S}} S ˉ Q \mathbf{Q} Q M × r M \times r M × r R \mathbf{R} R r × r r \times r r × r O ( r 3 ) \mathcal{O}(r^3) O ( r 3 ) Σ ^ M \hat{\boldsymbol{\Sigma}}_M Σ ^ M K ^ \hat{\mathbf{K}} K ^
当 σ 2 ∈ ( 0 , ∞ ) \sigma^2 \in (0, \infty ) σ 2 ∈ ( 0 , ∞ )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 ∥ Σ ^ M − σ 2 V ˉ − S ˉ K S ˉ ′ ∥ \|\hat{\boldsymbol{\Sigma}}_M − \bar{\boldsymbol{\Sigma}}_M(\mathbf{K}, \sigma^2)\| = \| \hat{\boldsymbol{\Sigma}}_M − \sigma^2 \bar{\mathbf{V}} − \bar{\mathbf{S}} \mathbf{K} \bar{\mathbf{S}}^{\prime}\|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 ∥ Σ ^ M − σ 2 V ˉ − S ˉ K S ˉ ′ ∥
产生的最佳参数估计(假设 σ 2 \sigma^2 σ 2
K ^ = R − 1 Q ′ ( Σ ^ M − σ 2 V ˉ ) Q ( R − 1 ) ′ (3.8) \mathbf{ \hat{K} = R^{−1} Q^{\prime} (\hat{\boldsymbol{\Sigma}}_M − \sigma^2 \bar{\mathbf{V}}) Q(R^{−1})^{\prime}} \tag{3.8}
K ^ = R − 1 Q ′ ( Σ ^ M − σ 2 V ˉ ) Q ( R − 1 ) ′ ( 3.8 )
相应的拟合后协方差矩阵是 Σ ˉ M ( K ^ , σ 2 ) \bar{\boldsymbol{\Sigma}}_M (\hat{\mathbf{K}}, \sigma^2 ) Σ ˉ M ( K ^ , σ 2 )
Σ ^ M ( K ^ , σ 2 ) = Q Q ′ ( Σ ^ M − σ 2 V ˉ ) Q Q ′ + σ 2 V ˉ = Q Q ′ Σ ^ M Q Q ′ + σ 2 ( V ˉ − Q Q ′ V ˉ Q Q ′ ) (3.9) \hat{\boldsymbol{\Sigma}}_M(\hat{\mathbf{K}}, \sigma^2 ) = \mathbf{QQ^{\prime}(\hat{\boldsymbol{\Sigma}}_M − \sigma^2 \bar{\mathbf{V}}) QQ^{\prime} + \sigma^2 \bar{\mathbf{V}}}\\
= \mathbf{QQ^{\prime} \hat{\boldsymbol{\Sigma}}_M QQ^{\prime} + \sigma^2 (\bar{\mathbf{V}} − QQ^{\prime} \bar{\mathbf{V}} QQ^{\prime})} \tag{3.9}
Σ ^ M ( K ^ , σ 2 ) = Q Q ′ ( Σ ^ M − σ 2 V ˉ ) Q Q ′ + σ 2 V ˉ = Q Q ′ Σ ^ M Q Q ′ + σ 2 ( V ˉ − Q Q ′ V ˉ Q Q ′ ) ( 3.9 )
此时,可以通过关于 σ 2 ∈ ( 0 , ∞ ) \sigma^2 \in (0, \infty ) σ 2 ∈ ( 0 , ∞ ) σ 2 \sigma^2 σ 2
∥ Σ ^ M − Σ ˉ M ( K ^ , σ 2 ) ∥ 2 = ∑ j , k { ( Σ ^ M − P ( Σ ^ M ) ) j k − σ 2 ( V ˉ − P ( V ˉ ) ) j k } 2 \|\hat{\boldsymbol{\Sigma}}_M − \bar{\boldsymbol{\Sigma}}_M (\hat{\mathbf{K}}, \sigma^2)\|^2 = \sum_{j,k} \{( \hat{\boldsymbol{\Sigma}}_M − \mathbf{P}(\hat{\boldsymbol{\Sigma}}_M ))_{jk} − \sigma^2 (\bar{\mathbf{V}} − \mathbf{P} (\bar{\mathbf{V}}))_{jk} \}^2
∥ Σ ^ M − Σ ˉ M ( K ^ , σ 2 ) ∥ 2 = j , k ∑ {( Σ ^ M − P ( Σ ^ M ) ) jk − σ 2 ( V ˉ − P ( V ˉ ) ) jk } 2
其中对于任何 M × M M \times M M × M A \mathbf{A} A P ( A ) ≡ Q Q ′ A Q Q ′ \mathbf{P(A) \equiv QQ^{\prime} A QQ^{\prime}} P ( A ) ≡ Q Q ′ AQ Q ′ O ( M 3 ) \mathcal{O}(M^3) O ( M 3 ) σ 2 \sigma^2 σ 2
K = R − 1 Q ′ ( Σ ^ M − σ ^ 2 V ˉ ) Q ( R − 1 ) ′ (3.10) \mathbf{K = R^{−1} Q^{\prime} (\hat{\boldsymbol{\Sigma}}_M − \hat{\sigma}^2 \bar{\mathbf{V}}) Q (R^{−1})^{\prime}} \tag{3.10}
K = R − 1 Q ′ ( Σ ^ M − σ ^ 2 V ˉ ) Q ( R − 1 ) ′ ( 3.10 )
对于 r < M r<M r < M O ( M 3 ) \mathcal{O}(M^3) O ( M 3 ) M M M n n n O ( n r 2 ) \mathcal{O}(nr^2) O ( n r 2 ) 第 4 节的时序数据比较。
最后,利用 K ^ \hat{\mathbf{K}} K ^ σ ^ 2 \hat{\sigma}^2 σ ^ 2 式(2.16) – 式(2.18) 即可。由此产生的 FRK 仅涉及 r × r r \times r r × r n × n n \times n n × n
(3)使用加权范数作为目标函数
应当为变化较小或数据较多的箱赋予更多权重。因此考虑如下加权 Frobenius 范数: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a 2 ≡ ∑ j , k a j a k { ( Σ ^ M ) j k − ( Σ ˉ M ( K , σ 2 ) ) j k } 2 (3.11) \|\hat{\boldsymbol{\Sigma}}_M −\bar{\boldsymbol{\Sigma}}_M (\mathbf{K}, \sigma^2 )\|^2_a \equiv \sum_{j,k} a_ja_k \{(\hat{\boldsymbol{\Sigma}}_M)_{jk} − (\bar{\boldsymbol{\Sigma}}_M(K, \sigma^2 ))_{jk}\}^2 \tag{3.11}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a 2 ≡ j , k ∑ a j a k {( Σ ^ M ) jk − ( Σ ˉ M ( K , σ 2 ) ) jk } 2 ( 3.11 )
其中 a 1 , … , a M a_1,\ldots ,a_M a 1 , … , a M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a 2 = ∥ A ˉ 1 / 2 Σ ^ M A ˉ 1 / 2 − A ˉ 1 / 2 Σ ˉ M ( K , σ 2 ) A ˉ 1 / 2 ∥ 2 \|\hat{\boldsymbol{\Sigma}}_M −\bar{\boldsymbol{\Sigma}}_M (\mathbf{K}, \sigma^2)\|^2_a = \|\bar{\mathbf{A}}^{1/2} \hat{\boldsymbol{\Sigma}}_M \bar{\mathbf{A}}^{1/2} − \bar{\mathbf{A}}^{1/2} \bar{\boldsymbol{\Sigma}}_M (\mathbf{K}, \sigma^2) \bar{\mathbf{A}}^{1/2}\|^2
∥ Σ ^ M − Σ ˉ M ( K , σ 2 ) ∥ a 2 = ∥ A ˉ 1/2 Σ ^ M A ˉ 1/2 − A ˉ 1/2 Σ ˉ M ( K , σ 2 ) A ˉ 1/2 ∥ 2
其中 A ˉ ≡ diag ( a 1 , … , a M ) \bar{\mathbf{A}} \equiv \operatorname{diag}(a_1,\ldots ,a_M) A ˉ ≡ diag ( a 1 , … , a M ) { a j : j = 1 , … , M } \{a_j : j = 1,\ldots ,M\} { a j : j = 1 , … , M } Σ ^ M \hat{\boldsymbol{\Sigma}}_M Σ ^ M Σ ˉ M ( K , σ 2 ) \bar{\boldsymbol{\Sigma}}_M (\mathbf{K}, \sigma^2) Σ ˉ M ( K , σ 2 ) 附录 A 中的表达式 (A.5),我们从统计上的选择是
a j ∝ ( w j ′ 1 n ) 1 / 2 / V D ( u j ) , j = 1 , … , M a_j \propto (\mathbf{w}^{\prime}_j \mathbf{1}_n)^{1/2} / \mathbf{V}_D(\mathbf{u}_j), j = 1,\ldots ,M
a j ∝ ( w j ′ 1 n ) 1/2 / V D ( u j ) , j = 1 , … , M
这是一个基于数据的权重,其中 V D ( u j ) \mathbf{V}_D(\mathbf{u}_j) V D ( u j ) j j j 附录 A 中的表达式 (A.1) 给出。
总之,K \mathbf{K} K σ 2 \sigma^2 σ 2 [4]
在高斯假设下,K \mathbf{K} K σ 2 \sigma^2 σ 2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 Σ ∣ |\boldsymbol{\Sigma}| ∣ Σ ∣ 式(2.16) 的 Sherman–Morrison–Woodbury 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协方差矩阵的逆 Σ − 1 \boldsymbol{\Sigma}^{-1} Σ − 1
类似的公式可以得到原始的协方差矩阵行列式:
∣ Σ ∣ = ∣ σ 2 V ∣ ∣ K ∣ ∣ K − 1 + S ′ ( σ 2 V ) − 1 S ∣ |\boldsymbol{\Sigma}|=|\sigma^2 \mathbf{V}| |K| |\mathbf{K}^{-1} + \mathbf{S}^{\prime}(\sigma^2 \mathbf{V})^{−1} \mathbf{S}|
∣ Σ ∣ = ∣ σ 2 V ∣∣ K ∣∣ K − 1 + S ′ ( σ 2 V ) − 1 S ∣
可以看出,该计算仅涉及 r × r r \times r r × r K \mathbf{K} K σ 2 \sigma^2 σ 2 K \mathbf{K} K [36] [11]
4 臭氧卫星数据固定秩克里金法
5 讨论
本文介绍了大规模空间数据集的精确克里金法(空间 BLUP)方法。从计算成本来看,FRK 是线性可扩展的,可以处理海量数据集(千兆字节量级)。我们的结果依赖于 使用一类源自空间随机效应模型的非平稳协方差函数 。回想一下 式(2.12):
C ( u , v ) ≡ S ( u ) ′ K S ( v ) , u , v ∈ R d , C(\mathbf{u,v}) \equiv \mathbf{S(\mathbf{u})^{\prime} K S(\mathbf{v})}, \qquad \mathbf{u, v} \in \mathbb{R}^d,
C ( u , v ) ≡ S ( u ) ′ KS ( v ) , u , v ∈ R d ,
其中 S ( ⋅ ) ≡ ( S 1 ( ⋅ ) , … , S r ( ⋅ ) ) ′ \mathbf{S}(\cdot) \equiv (S_1(\cdot),\ldots ,S_r(\cdot))^{\prime} S ( ⋅ ) ≡ ( S 1 ( ⋅ ) , … , S r ( ⋅ ) ) ′ r × r r \times r r × r K \mathbf{K} K K \mathbf{K} K K \mathbf{K} K Y ( ⋅ ) Y(\cdot) Y ( ⋅ ) ε ( ⋅ ) \varepsilon(\cdot) ε ( ⋅ ) σ 2 \sigma^2 σ 2
贝叶斯分析还允许在非线性地统计模型(Diggle 等 (1998 [9] 式(2.12) 来实现计算加速。作为这方面的证据,Hrafnkelsson 和 Cressie (2003 [17] 5 5 5
(隐)Y Y Y 式(2.6) 中包含另一个对角矩阵来建模。当两个对角矩阵彼此成比例时,测量误差参数 σ 2 \sigma^2 σ 2 τ 2 \tau^2 τ 2 τ 2 + σ 2 \tau^2 + \sigma^2 τ 2 + σ 2 Y ( ⋅ ) Y(\cdot) Y ( ⋅ ) τ 2 = 0 \tau^2 = 0 τ 2 = 0
由 式(2.12) 给出的非平稳协方差函数具有显著的支持度变化特性。令 B ⊂ R d B \subset \mathbb{R}^d B ⊂ R d Y ( B ) ≡ ∫ B Y ( s ) d s = ∣ B ∣ Y(B) \equiv \int_B Y(\mathbf{s}) d \mathbf{s}=|B| Y ( B ) ≡ ∫ B Y ( s ) d s = ∣ B ∣ ∣ B ∣ |B| ∣ B ∣ B B B d d d
cov { Y ( B 1 ) , Y ( B 2 ) } = S ( B 1 ) ′ K S ( B 2 ) , B 1 , B 2 ⊂ R d , \operatorname{cov}\{Y(B_1), Y(B_2)\} = \mathbf{S}(B_1)^{\prime} \mathbf{KS}(B_2), B_1, B_2 \subset \mathbb{R}^d,
cov { Y ( B 1 ) , Y ( B 2 )} = S ( B 1 ) ′ KS ( B 2 ) , B 1 , B 2 ⊂ R d ,
其中 S ( B ) ≡ ( S 1 ( B ) , … , S r ( B ) ) ′ \mathbf{S}(B) \equiv (S_1(B),\ldots,S_r(B))^{\prime} S ( B ) ≡ ( S 1 ( B ) , … , S r ( B ) ) ′ S l ( B ) ≡ ∫ B S l ( s ) d s = ∣ B ∣ S_l(B) \equiv \int_B S_l(\mathbf{s}) d \mathbf{s}= |B| S l ( B ) ≡ ∫ B S l ( s ) d s = ∣ B ∣ B ⊂ R d B \subset \mathbb{R}^d B ⊂ R d
因此,无论数据和预测变量的支撑如何,克里金方程都采用与 式(2.16) – (2.18) 相同的形式。实际上,基本功能将离线集成。
最后,从第 3.2 节中给出的空间随机效应模型 ν ( s ) = S ( s ) ′ η ν(\mathbf{s}) = \mathbf{S}(\mathbf{s})^{\prime} \boldsymbol{\eta} ν ( s ) = S ( s ) ′ η ν ( s , t ) = S ( s ) ′ η ( t ) ν(\mathbf{s}, t) = \mathbf{S}(\mathbf{s})^{\prime} \boldsymbol{\eta}(t) ν ( s , t ) = S ( s ) ′ η ( t ) { η ( t ) : t = 0 , 1 , 2 , … } \{\boldsymbol{\eta}(t) : t = 0, 1, 2,\ldots \} { η ( t ) : t = 0 , 1 , 2 , … } 0 0 0 cov { η ( t 1 ) , η ( t 2 ) } ≡ K ( t 1 , t 2 ) \operatorname{cov} \{\boldsymbol{\eta}(t_1), \boldsymbol{\eta}(t_2)\} \equiv \mathbf{K} (t_1, t_2) cov { η ( t 1 ) , η ( t 2 )} ≡ K ( t 1 , t 2 ) t 1 , t 2 = 0 , 1 , 2 , … t_1, t_2 = 0, 1, 2,\ldots t 1 , t 2 = 0 , 1 , 2 , …
参考文献
[1] Adler, R. J. (1981) The Geometry of Random Fields. Chichester: Wiley. [2] Billings, S. D., Beatson, R. K. and Newsam, G. N. (2002a) Interpolation of geophysical data using continuous global surfaces. Geophysics, 67, 1810–1822. [3] Billings, S. D., Newsam, G. N. and Beatson, R. K. (2002b) Smooth fitting of geophysical data using continuous global surfaces. Geophysics, 67, 1823–1834. [4] Cressie, N. (1985) Fitting variogram models b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J. Int. Ass. Math. Geol., 17, 563–586. [5] Cressie, N. (1989) Geostatistics. Am. Statistn, 43, 197–202. [6] Cressie, N. (1990) The origins of kriging. Math. Geol., 22, 239–252. [7] Cressie, N. (1993) Statistics for Spatial Data, revised edn. New York: Wiley. [8] Cressie, N. and Johannesson, G. (2006) Spatial prediction of massive datasets. In Proc.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Elizabeth and Frederick White Conf ., pp. 1–11. Canberra: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9] Diggle, P. J., Tawn, J. A. and Moyeed, R. A. (1998) Model-based geostatistics. Appl. Statist., 47, 299–326. [10] Donoho, D. L., Mallet, S. and von Sachs, R. (1998) Estimating covariances of locally stationary processes: rates of convergence of best basis methods. Technical Report 517.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11] Fuentes, M. (2007) Approximate likelihoods for large irregularly spaced spatial data. J. Am. Statist. Ass., 102, 321–331. [12] Furrer, R., Genton, M. G. and Nychka, D. (2006) Covariance tapering for interpolation of large spatial datasets. J. Computnl Graph. Statist., 15, 502–523. [13] Haas, T. C. (1995) Local prediction of a spatio-temporal proces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wet sulfate deposition. J. Am. Statist. Ass., 90, 1189–1199. [14] Hastie, T. (1996) Pseudosplines. J. R. Statist. Soc. B, 58, 379–396. [15]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2001)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New York: Springer. [16] Henderson, H. V. and Searle, S. R. (1981) On deriving the inverse of a sum of matrices. SIAM Rev., 23, 53–60. [17] Hrafnkelsson, B. and Cressie, N. (2003) Hierarchical modeling of count data with application to nuclear fall-out. Environ. Ecol. Statist., 10, 179–200. [18] Huang, H.-C., Cressie, N. and Gabrosek, J. (2002) Fast, resolution-consistent spatial prediction of global processes from satellite data. J. Computnl Graph. Statist., 11, 63–88. [19] Johannesson, G. and Cressie, N. (2004a) Variance-covariance modeling and estimation for multi-resolution spatial models. In geoENV IV—Geostatistics for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eds X. Sanchez-Vila, J. Carrera and J. Gomez-Hernandez), pp. 319–330. Dordrecht: Kluwer. [20] Johannesson, G. and Cressie, N. (2004b) Finding large-scale spatial trends in massive, global, environmental datasets. Environmetrics, 15, 1–44. [21] Johannesson, G., Cressie, N. and Huang, H.-C. (2007) Dynamic multi-resolution spatial models. Environ. Ecol. Statist., 14, 5–25. [22] Journel, A. G. and Huijbregts, C. (1978) Mining Geostatistics. London: Academic Press. [23] Kammann, E. E. and Wand, M. P. (2003) Geoadditive models. Appl. Statist., 52, 1–18. [24] London, J. (1985) The observed distribution of atmospheric ozone and its variations. In Ozone in the Free Atmosphere (eds R. C. Whitten and S. S. Prasad), pp. 11–80.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25] Madrid, C. R. (1978) The Nimbus-7 User’s Guide. Greenbelt: NASA. [26] Matheron, G. (1962) Traite de Geostatistique Appliqueé, vol. I. Paris: Technip. [27] Matheron, G. (1963) Principles of geostatistics. Econ. Geol., 58, 1246–1266. [28] McPeters, R. D., Bhartia, P. K., Krueger, A. J., Herman, J. R., Schlesinger, B. M., Wellemeyer, C. G., Seftor, C. J., Jaross, G., Taylor, S. L., Swissler, T., Torres, O., Labow, G., Byerly, W. and Cebula, R. P. (1996) The Nimbus-7 Total Ozone Mapping Spectrometer (TOMS) Data Products User’s Guide. Greenbelt: NASA. [29] Nychka, D. (2000) Spatial-process estimates as smoothers. In Smoothing and Regression: Approaches,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 (ed. M. G. Schimek), pp. 393–424. New York: Wiley. [30] Nychka, D., Bailey, B., Ellner, S., Haaland, P. and O’Connell, M. (1996) FUNFITS: Data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ools for Estimating Functions. Raleigh: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31] Nychka, D., Wikle, C. and Royle, J. A. (2002) Multiresolution models for nonstationary spatial covariance functions. Statist. Modllng, 2, 315–331. [32] Quiñonero-Candela, J. and Rasmussen, C. E. (2005) A unifying view of sparse approximate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J. Mach. Learn. Res., 6, 1939–1959. [33] Rue, H. and Tjelmeland, H. (2002) Fitting Gaussian Markov random fields to Gaussian fields. Scand. J. Statist., 29, 31–49. [34] Sahr, K. (2001) DGGRID Version 3.1b: User Documentation for Discrete Global Grid Generation Software. Ashland: 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 (Available from http://www.sou.edu/cs/sahr/dgg/.) [35] Shi, T. and Cressie, N. (2007) Glob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ISR aerosol data: a massive data product from NASA’s Terra satellite. Environmetrics, 18, 665–680. [36] Stein, M. (2008) A modeling approach for large spatial datasets. J. Kor. Statist. Soc., 37, in the press. [37] Stroud, J. R., Müller, P. and Sansó, B. (2001) Dynamic models for spatiotemporal data. J. R. Statist. Soc. B, 63, 673–689. [38] Tzeng, S., Huang, H.-C. and Cressie, N. (2005) A fast, optimal spatial-prediction method for massive datasets. J. Am. Statist. Ass., 100, 1343–1357. [39] Vidakovic, B. (1999) Statistical Modeling by Wavelets. New York: Wiley. [40] Wahba, G. (1990) Spline Models for Observational Data. Philadelphia: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